Oanghai078 - 2021/9/18 4:34:23
水仙
【导读】这个冬天,有了水仙花的陪伴便少了几份寂寞,多了几份快乐和希望。望着水仙花,我似乎感受到春天在向我走来,树海读书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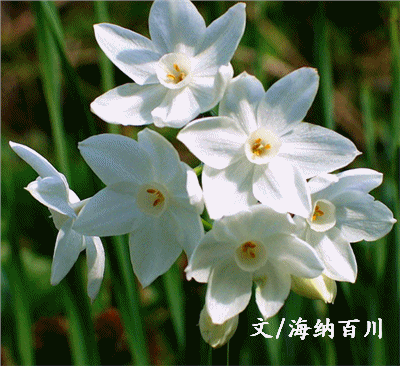
那天,我陪女友在街上闲逛,在一条小街道旁边看见了一个卖花的人。这个人年过四十,朴素大方,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在远处,爱看读书阁,我们就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他的花种得不错。
女友对我说,过去看看吧,我们便去了。平时并不是一个爱花的人,除了菊花和美人蕉,我竟叫不出几种花的名字。女友陶醉花与叶的世界里,华闻读书阁,我的视线却被一小堆“大蒜头&rdquo,树海读书阁;所吸引。黑乎乎的,树海读书阁,上面裹满了泥巴。我很好奇,就问卖花人那是什么东西,他告诉我是水仙。我很诧异,我很难把刚才这黑乎乎的东西跟这么动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想起一句歌词:&ldquo,铭华读书阁;你说我冷的像水仙,精彩读书阁,只有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种”我想,金霏读书阁,水仙只有在冰冷的冬天才能开放吧。
水仙花什么样子,我还没有看见过。于是我买下了几粒种子,把它们的“黑衣”脱掉,孔子读书阁,然后装进一个很普通的碗里,倒进一些清水,最后把花瓶放到了办公桌上。
种下了几粒种子,树海读书阁,就多了几分期待,孔子读书阁。每天上班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水仙发芽了没有。没过几天我便惊喜的发现在白白的&ldquo,金霏读书阁;大蒜头”上冒出来几个嫩芽,绿绿的,就像一个个小脑袋,伸出来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大蒜头”的下面长出很多白胡子,我知道那是水仙的根须。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水仙在一天天成长,我在一天天地期待,不到两周,水仙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碧绿,娇嫩,这便成了我办公桌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引来一片赞叹,让我欣喜不已。女友打来电话,问我水仙花开花了没有,我说应该快了。我一直想象这水仙花开的颜色,是粉红,洁白还是淡绿?我不知道,让这位花姑娘自己告诉我吧。
那天,外面飘着雪花,很冷,我早早就往办公室赶。推开门,打了几个哆嗦,然后匆匆地把带的几本书往办公桌上一放,这时我惊喜的发现,在绿叶之间,竟出现了几个绿中带黄的花蕾。我的水仙快要开花了,那一瞬间,我真想把我的激动和喜悦与全世界分享。
又过了几天,一进办公室一个同事就高兴地叫我,“小钟,快来看啊,你的水仙开花了,好漂亮哦!”水仙花开了,像星星一样,洒在一块碧玉上,璀璨而晶莹,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但高雅而不低俗,那淡黄的花瓣让人感到一丝丝温暖。这个冬天,有了水仙花的陪伴便少了几份寂寞,多了几份快乐和希望。望着水仙花,我似乎感受到春天在向我走来。
生活中,洒下希望的种子,我们便多了一份期待,多了一片收获,多了一种幸福。
【责任编辑:敏敏】
相关的主题文章:
再见知己
一池秋水
一生烛照永恒
谁能真正做到顺其自然?
下雨的日子_2
【导读】这个冬天,有了水仙花的陪伴便少了几份寂寞,多了几份快乐和希望。望着水仙花,我似乎感受到春天在向我走来,树海读书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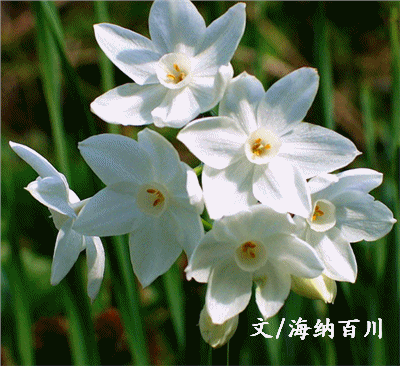
那天,我陪女友在街上闲逛,在一条小街道旁边看见了一个卖花的人。这个人年过四十,朴素大方,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在远处,爱看读书阁,我们就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他的花种得不错。
女友对我说,过去看看吧,我们便去了。平时并不是一个爱花的人,除了菊花和美人蕉,我竟叫不出几种花的名字。女友陶醉花与叶的世界里,华闻读书阁,我的视线却被一小堆“大蒜头&rdquo,树海读书阁;所吸引。黑乎乎的,树海读书阁,上面裹满了泥巴。我很好奇,就问卖花人那是什么东西,他告诉我是水仙。我很诧异,我很难把刚才这黑乎乎的东西跟这么动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想起一句歌词:&ldquo,铭华读书阁;你说我冷的像水仙,精彩读书阁,只有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种”我想,金霏读书阁,水仙只有在冰冷的冬天才能开放吧。
水仙花什么样子,我还没有看见过。于是我买下了几粒种子,把它们的“黑衣”脱掉,孔子读书阁,然后装进一个很普通的碗里,倒进一些清水,最后把花瓶放到了办公桌上。
种下了几粒种子,树海读书阁,就多了几分期待,孔子读书阁。每天上班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水仙发芽了没有。没过几天我便惊喜的发现在白白的&ldquo,金霏读书阁;大蒜头”上冒出来几个嫩芽,绿绿的,就像一个个小脑袋,伸出来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大蒜头”的下面长出很多白胡子,我知道那是水仙的根须。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水仙在一天天成长,我在一天天地期待,不到两周,水仙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碧绿,娇嫩,这便成了我办公桌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引来一片赞叹,让我欣喜不已。女友打来电话,问我水仙花开花了没有,我说应该快了。我一直想象这水仙花开的颜色,是粉红,洁白还是淡绿?我不知道,让这位花姑娘自己告诉我吧。
那天,外面飘着雪花,很冷,我早早就往办公室赶。推开门,打了几个哆嗦,然后匆匆地把带的几本书往办公桌上一放,这时我惊喜的发现,在绿叶之间,竟出现了几个绿中带黄的花蕾。我的水仙快要开花了,那一瞬间,我真想把我的激动和喜悦与全世界分享。
又过了几天,一进办公室一个同事就高兴地叫我,“小钟,快来看啊,你的水仙开花了,好漂亮哦!”水仙花开了,像星星一样,洒在一块碧玉上,璀璨而晶莹,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但高雅而不低俗,那淡黄的花瓣让人感到一丝丝温暖。这个冬天,有了水仙花的陪伴便少了几份寂寞,多了几份快乐和希望。望着水仙花,我似乎感受到春天在向我走来。
生活中,洒下希望的种子,我们便多了一份期待,多了一片收获,多了一种幸福。
【责任编辑:敏敏】
相关的主题文章:
再见知己
一池秋水
一生烛照永恒
谁能真正做到顺其自然?
下雨的日子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