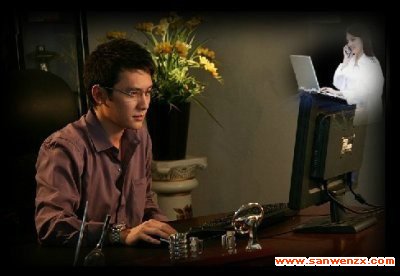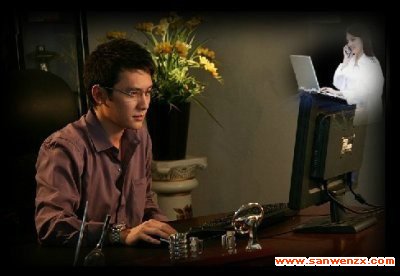那些回忆
常常想起年少时在家乡求学的那段漫长时光。那些回忆,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是那么平淡淳朴,就像一瓶醇酒,深藏在心间的地窖里,经过岁月的发酵,不曾淡去,只是历久弥新,偶尔搬出来呷一口,香甜四溢。
1
还记得那年的一个清晨,母亲把一个自己用粗布缝制的布袋子跨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把我送到不远处的村小学。这已经成了一个灰色的影象,永远烙在我记忆的天空,
金门读书阁。可能是我启蒙比较晚,次晨此景成了我有完整和系统记忆以来的存储开端。那个书包陪伴我度过了整整四年时光,直至我到中心小学读高年级。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我都不知道世上还有彩色好看的书包存在。村子里的小伙伴大都挎着这样的布包。布袋里总是装着两本书:一本语文书,一本数学书,还有一只铅笔。我就这样挎着那个黑色的布袋子,踩在村子里蜿蜒如蚯蚓的黄土路上,在学校和家里的两点一线间奔波。
那一年,我学会了10个数字,在祖屋黄土垒成的墙壁上用石块重重刻下了“1995”,作为我步入漫长书山之路的起点,
树海读书阁。时隔多年,世事沧桑,空置多年摇摇欲坠的老屋墙壁上那几个歪歪斜斜,蚯蚓一样扭曲稚嫩的数字还留在斑驳颓废的墙面上,我却已经长成大人。
那些年,在那个闭塞的大山里,我们没有很多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零食。体育课上老师教会我们的就是“老鹰抓小鸡”“捉迷藏”之类。私下里男生会在黄土铺成的操场上滚铁环、抽陀螺,女生会跳绳、丢手绢,大家玩得乐此不彼,仿佛那就是天底下最好玩的事情。尘土飞扬的操场两端孤零零地矗立着两个木头搭成的篮球架子,已经摇摇欲坠。从来没有人打过篮球。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神物,好像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长在那里一样,没有人关心。
村小的校舍很简陋,是一排砖砌的平房,房顶覆盖着乌黑的瓦片。火红的砖墙裸露在外,砖缝间是凝固的白色石灰浆,现在看来很有一种复古的艺术感。那排平房尽头的檩子下挂着一个铁打的铃铛,比走江湖的道士腰间挂的大很多很多。上下课和放学时,老师会拽着铃铛下的麻绳摇动,清越的铃声于是“铛铛”响起,
华闻读书阁,于是我们就像僵尸片中的小鬼一样,在招魂的铃声中或聚或散。三声是上课,六声是下课,急促的十声是紧急集合,约定俗成,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规定了。那个铃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平时老师不让靠近,就像他手中的红笔一样神圣。周末放假,老师们回家后,小伙伴常常偷偷跑到铃铛下,踮起脚尖,拽着铃铛上系着的麻绳,一通胡乱的摇晃,于是清脆的铃声胡乱响起,远远地飘荡开去,余音绕梁,久久不绝。大家伙儿心里是无比的激动,一种触碰圣物的兴奋和刺激,能让小小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只是现在再也没有这种类似的心动了,即使遇上曾经喜欢的女生。
课桌很古旧,松木的,留有深深浅浅的脉纹,是很高很大的桌子,
金霏读书阁,每个桌子两个屉子,可以坐两位小朋友。矮小的身躯,坐在高高的凳子上,要趴在桌面上,身体前倾才能写作业。桌面没有上漆,凸凹不平,写作业时只能垫上一本厚书。写完作业,书本上已经印上密密麻麻的铅笔印子,作业本俨然充当了复写纸的角色。教室前面雪白的石灰墙壁上用钉子悬挂着一个大木板,大概2米长,1米见宽的样子,涂上黑黑的油漆,就是黑板了。上课时,头发斑白的老师用颤抖的手臂握着短短的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教室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粉笔与木板亲密接触发出的“呲呲”的响声,黑板摇晃着与墙面碰撞的“丝丝”声,还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讲台上粉笔永远只有一种单调的白颜色。白色的字应和着黑色的板,还有黑色的铅笔芯,白花花的墙壁,非黑即白,泾渭分明,构成我们那个时候课堂的永恒的二原色。
那时候,老师一直写到只剩一个粉笔头,才舍得扔掉。没办法,条件简陋,在那个闭塞的世外桃源,搞到教学用品比搞到毒品还困难,因为罂粟果子只要在家里的菜园里撒下几粒种子就能得到,而一盒粉笔却要通过千里之外的县城运来。后来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望着画面上破旧的校舍,我脑海立刻浮现起这些场景。可能大山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吧,好在当时我们一个也没有缺席,
宁静读书阁,当真是“一个也不能少”。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教室,幼小懵懂的我们从一撇一捺开始,跟着老师黑板上的示教,一个字一个字模仿,开始了启蒙学习之旅,
精彩读书阁。老师其实都是村里稍有文化的人(一般是高中文化)充任的,
树海读书阁,很严厉,手里拿着一个竹棍做成的教鞭,上课时用来指示黑板上的字。要是谁上课走神,老师会拿竹条敲手背,小手通常会被敲打得红肿。向家长告状,也只是训斥自己不听话,活该,反是自取其辱。正是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之下,我学会了好多的数字和汉字,还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拼音字母。
那时,四个年级一百多号小朋友,三个老师,显然是有点仓促的。通常,一个教室会坐两个年级,
金霏读书阁。老师这边讲完了高年级的语文,会接着给低年级的同学讲数学,
树海读书阁。闲暇之余,常常好奇地偷听旁边高年级的课,
金门读书阁,虽然不甚了了,却有一丝对未知领域的渴望和好奇,也算得上另一种形式的蹭课了。
还记得小学校破旧的厕所里,课间休息时,我们在里面尿尿,常常站在地上握着小鸡鸡,把细细的尿液往墙壁上射,比谁的尿液射得高,长此以往,墙壁上黄土砌成的墙面都被腐蚀镂空,害得老师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和稀泥补破墙。那个贫穷的年代,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方式了。
没有专业的老师,还要贯彻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教育方针。老师们通常身兼多职,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历史统统教授,
广济读书阁。梦里,常常忆起年过半百的老师扯着五音不全的嗓门教我们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红》那些老掉牙的红歌的情形,不禁莞尔,
树海读书阁。体育课上,跳远就是在黄土的操场上挖个大坑,沙子都没有,大家直接往里面跳。跳高,就是在两个木头架子上横一根长竹竿,大家一个个鱼贯而出,越过那个竿子。关于球类运动,有段时间,曾经运来过几个排球,老师教过大家用双手把球顶起来,现在想起来,有点像海洋馆里海豚用尖尖的嘴巴把头上空的保龄球顶起来差不多。
操场一隅,有过一个乒乓球台,水泥砌成的,就是一个平台,有点类似于东北那边的土炕,经过多年风雨的侵蚀,已经坑坑洼洼的,就像癞蛤蟆身上的斑斑点点,凸凹不平。刚开始有大人们在那儿打球,后来嫌台面不平整,就鲜有光顾了。此处便成了我们的游乐园。我们握着自制的木板削成的拍子,在这儿玩得不亦乐乎。坑坑洼洼的台子,我们也闹得饶有滋味,像模像样。再差的环境里也能学得好的本领,我一手不凡的球技,就是在这里勤学苦练出来的。
那个年代,物质也实在是贫乏之极。甚至于一块小小的磁铁,也能引起我们的青睐,记得曾经两个伙伴因争抢一小块破碎的磁铁而争执受伤。那时,我们会咀嚼着5毛钱一包的方便面而津津有味,舔着一根2毛钱的老冰棍而志得意满。一瓶1块钱的汽水已经成为奢侈品了,堪比现在喝上一瓶百年老窖的喜悦感。
那时候没有零花钱买课外读物,我只看过一本别人的连环画《金刚葫芦娃》。夜里,守着黑白电视机看满是雪花点点的单调节目,也能看得兴致勃勃,一直到电视台停台,屏幕上显现斗大的“再见”才作罢,
树海读书阁。现在回忆起来,有点幼稚,也就那点出息了。
别人的童年,都是在幼儿园里骑着小木马,玩着玩具汽车度过的,我们却是在青山绿水中长大的。当别人在公园里骑着小木马,在游泳池里戏水时,我们正在山上的灌木丛间放狗逐兔,在小河里的清水中捉鱼摸虾。可是我们却仍旧天真地快乐着,没有一丝忧伤。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成长方式罢了。
2
后来小学四年级时,转到十几里外的中心小学寄宿。陌生的环境,
树海读书阁,远离父母的庇护,
爱看读书阁,倒没觉得什么不适应,可能我这人本来就没心没肺,只要活得好,呆哪儿都一样。
只是生活不适应,
铭华读书阁。简陋的宿舍,拿到现在来说,就是危房了。刚开始半个月,住房紧张,
树海读书阁,几十号人蜷缩在一个小平房内,全部打地铺,被子一床挨一床。后来被安排到N年前的土房子里,松散的木架子床,一翻身就吱呀吱呀响动,仿佛要散架了。那个屋里住着十多个男生,处在学校围墙外的操场旮旯里,远离围墙内的老师同学。人多床少,两个人睡一张床,肌肤相亲,耳鬓厮磨,竟也没有日久生情,擦出激情的火花来。电磁学上同性相斥的道理原来也适用于伟大的人类。
隔壁只住着一个烧锅炉的大师傅,垂垂老矣,古铜色的脸上被岁月的刀子刻上深沟浅壑,就像窗外起伏的梯田一样。现在想想,好后怕,幸亏当时民风淳朴,没有变态杀人狂,拿着电锯,上演一场午夜惊魂,否则我们就集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像当年曹操扔在赤壁的百万雄师一样,谈笑间灰飞烟灭了。古旧的老房子,鼠害横行,一到半夜里,就在墙壁间或房顶飞檐走壁,呼朋引伴。我们就这样与这群土著居民们同处一室,和平共处,堪称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经典案例。
遇到雷雨天气,风呀,雨呀,欢叫着往屋内窜,透过聚乙烯塑料装裱的窗户,或从屋顶某处破漏的瓦片俯冲而下,常常湿了被子,冲了鞋子。我记得,那时经常拿着脸盆去接漏下的雨水,就像接水龙头放出来的一样,我想后来英语课上学到的“pourcatanddog”(下猫和狗一样的倾盆大雨)也不过如此了吧。大雪纷飞的冬夜,当黄世仁甚至杨白劳和小白菜还都在屋里烤着火的时候,我们正蜷缩在冰冷的被子里,听着北风那个吹呀,肆无忌惮灌进屋子里,头都不敢伸出被子里。夏日里的太阳,就像赤道边上的一样,总是早出晚归,直射进来,火辣辣的,烤得屋子里热气腾腾,蒸桑拿一样。实在熬不住的时候,恨不能像后羿一样,拿个弓箭把太阳射下来。这里就是一个反季节空调,夏热冬冷,堪称人间地狱,我们在这里炼狱,所幸,最终浴火重生,修成正果,练得超强的忍耐力,像蟑螂小强一样耐得住恶劣环境。
山里的教育,条件总是简陋的。当时80多号人呆在一个大教室里,总算窗明几净,红墙绿瓦了。只是中华几千年以来的印刷术在这里还没有普及开来。学校没有印刷机,只有一个油印蜡板。每学期仅有的一次期中考试试卷,都是老师辛苦地用刀子刻在蜡板上,一笔一划,就像篆刻碑文一样,不知是回体还是颜体的书法龙飞凤舞的,看得我们这些门外汉云里雾里,只能估摸着踹度,实在不认识就只好求助于监考老师。即便如此,发下来的试卷上,还有好多字不清晰,还要在老师的口头更正中,自己一笔一划地还原真面目。此种情况下,要想得到多余的复印资料似乎不可能了。
记得语文课上,老师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码字,我们在作业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复制,辛辛苦苦地,抄满一篇数千字的短文,常常花费一节课时间,占去好几页作业纸,而结果仅仅是为了回答后面三五个阅读问题,其辛苦不言而喻,可是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坚持抄下来了。抄文章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字,记住了不少的故事,从故事中学得不少道理,也算一举多得,不枉当一回抄书公了。
开始接受科学知识洗礼,貌似也开始显现出对未知科学领域的些许探究兴趣。学了简单的电磁学后,开始迷恋电动东西,从废旧的复读机里抠出小电机,接上五号电池,安放在泡沫板上,再装上小药瓶上的橡胶塞做成的车轮子,用橡皮筋充当传送带,竟然也做成一个水陆两栖船,像我胸口剧烈跳动的心一样,在水面“突突”地远航,想要漂洋过海,在外面广阔的天地一展身手。可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
爱看读书阁,这些兴趣得不到很好的引导和关注,就像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得不到阳光雨露的好好滋润,过早地夭折了。
生活条件的确清苦啊。办学条件限制,中心校没有学生食堂,饭菜自理。学校筑了一个大灶,四四方方的灶壁,内嵌一口大铁锅,装上水,盖上木板,同学们自己把饭盒里装上水和米,放在灶里蒸熟,
树海读书阁。菜嘛,自己从家里带,冷菜就着热饭,凑合凑合得了。初来乍到时候,猪一样能吃,不会算计着过日子,竟然两天内把一盆的瘦肉给吃完啦。接下来断粮数日,狠狠地体验了一把当年孔圣人困于陈蔡绝境绝粮断食的日子,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深深明白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
而且那灶里的水也是二次利用,作为我们的洗浴用水。犹记得,黄昏余晖下,或者晨光熹微中,我们披着日光,拿个脸盆,到灶台边,由大师傅给舀水。然后就着水龙头洗脸或洗脚。记得,这开水是免费奉送的,
精彩读书阁,那蒸饭也是不收钱的。想想如今的中心校已经建起学生食堂,学生刷卡吃饭,不知我们那拨是幸运的一茬,还是不幸的一撮呢?
学生义务劳动一直是学校创收的主要方式。老师们每年夏天都会组织学生去附近的茶场采茶,以补贴学校建设之用,持续半个月之久,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劳动实践。我们在炎炎烈日下的茶树棵子间忙碌,蜜蜂采蜜一样井井有序。流火的六月,火球一样毒辣的太阳,晒得人黑黝黝的,
修身读书阁,远远望去,像非洲黑奴一样。多年后,抚摸着手臂上黝黑的深入骨髓的肌肤,还唏嘘不已:晒晒更健康啊。
即使现在,每次路过那个熟悉的学校,看着那山岗上依旧孤零零矗立着的略显寒碜和孤单的一排排破旧的房子,依旧心有戚戚然。此时,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袭上心头,唤醒我那沉寂已久的回忆,一切,恍若昨日。可是时光已经走远,我已回不到当年。
3
初中是在镇上读完的。
作为唯一的初中,当地最高学府,镇中条件的确好多了,可也只是好那么一点点。教室更宽敞了,宿舍更安全了,老师水平更高了。人民教教序列中,出现了些许大学学历的天之骄子,但是中流砥柱仍然是中师毕业的大多数。
开始学英语了,从ABC开始。发音不准的老师把China发音成“钱呢”,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从一窍不通到能够看懂简单的英文。当时我们英语老师是某师范大学毕业生,听说英语过了4级,当时很崇拜呀。其实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因为现在我也是考过四级的老人了,而且我已能把China发音发得很标准。成长真是有趣,短短的数十年,
孔子读书阁,伴随着身体的突飞猛长,能力和学识也像雨后的竹笋一样拔节疯长,已经超越当年的偶像,攀上当时看来似乎遥不可及的高山。
当时我们就是一群山沟沟里的青蛙,坐井观天,狭窄的视线始终穿透不了重山峻岭之外的那一线天。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政治课上,讲到资本主义的落后性时,土生土长的老师立即用手指着窗外澄澈如洗的蓝天和远处连绵起伏的青山,激情澎湃地说:“看,我们社会主义的天永远是蓝的,水永远是绿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城市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工烟囱永远排放这黑黑的烟雾厂的废气。资本家都不是人,他们宁愿把大桶的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们喝。”当时懵懂的我笃信不已,后来当我来到城里,看到都市里浓密的雾霾颗粒在太阳光的直射中发出诡异的色彩时,在新闻里了解到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浪潮中,我们的作为先进阶级代表的奶农把大量囤积变质的鲜奶成桶倒掉时,我才意识到环境污染和生产过剩是所有工业化革命中的国家都要付出的惨痛代价,与政治体制无关,
孔子读书阁。不能怪兢兢业业的老师,他也是久居深山的青蛙。只有走出了大山,青蛙才能变王子。
不会忘记,学校旁边的那个泥土铺就的操场。没有水泥地面,没有草皮铺垫,乱七八糟地矗立着的锈迹斑斑的双杠,坐在上面能沾一身铁锈。角落的篮球架子也是久经风雨,摇摇欲坠。一到雨天,泥泞不堪的操场就成了一锅浆糊,黏黏的,黄黄的,踩在上面如同踩在泥塘里一样,溅得一身的泥浆。那个所谓的运动场,其实远比不上如今城里的任何一个社区健身场地。每天,
精彩读书阁,晨光熹微中,成百上千的学生围着泥土的操场跑道晨跑,也颇有点浩浩荡荡的气势,看上去就像一条蜿蜒的巨蟒,首尾相连,蜷成一团。记忆仍停留在这些,只是如今的操场已经扩建改造,铺上绿绿的草皮,还装上了钢筋护栏,焕然一新。
还记得简陋的公共厕所里,
孔子读书阁,成千上万的蛆虫从化粪池里爬出来,在暖暖的阳光里,悠闲地蠕动着,享受着午后宁静的小时光。有些爬上高高的墙壁,
树海读书阁,直至死去成蛹,再破蛹成蚊,扑愣着翅膀飞起。走在厕所地面上时,不小心踩碎的幼虫噼里啪啦的脆响,就像爆米花一样,裸露出丰富的蛋白质肉肉来,白花花的;还好,心理素质好,刚吃进去尚未消化的食物没有从嘴巴里排泄出来。突然挺想念这些蚊子的幼虫们(学名应该叫孑孓吧----当时的初中生物书上说的),不知道现在厕所地板上还有没有它们熟悉的身影。
不知,半夜里,厕所边的那盏昏黄黯淡的白炽路灯下,还有没有像我一样很傻很天真的少年,矗立刺骨寒风中举着作业本苦思冥想该如何证明被乱七八糟的直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圆里面,某两条线段的长度相等。我想,时代虽然在变化,大山里,不畏清苦,囊萤映雪的精神却是亘古不变的,埋头苦读的淳朴后生还是不可或缺的。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我也早被甩在沙滩上风干了------迷失在城里多彩的霓虹下,当年的志气和勇气早已经荡然无存。如果时光倒流,再回到那个艰苦的环境,我恐怕再吃不起那份苦了。
不会忘记,那些临近中考的日子里,每天傍晚,与CCTV新闻联播同步开播的班会上,班主任老师苦口婆心、唾液四溅的教导:“你们只有好好学习,考上高中,再上大学,才能跳出大山,逃脱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生活。”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的我,懵懵懂懂中,或多或少受到那一番慷慨激扬的游说的蛊惑,于是发愤图强,上了高中,接受了所谓的高等教育,成了大学规模化人才生产线上批量化生产出来的一个残次品,然后披着一身狼皮去水泥丛林中和遍地的狮子老虎抢食吃。老师那番苦口婆心的说教尽管有着意欲提升学校升学率的“不良”动机,但不可否认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对后生晚辈的一番好意和些许期许。毕竟他们没有像急功近利的高中老师一样用“好好学习,考名牌大学,娶美女,开大奔,当老板“之类明显世俗和势利的说词来误导我们,给我们画一个永远充不了饥的大饼。因为,只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的愿望的确轻而易举就能实现。
去年年关回家,车上偶遇初三时的数学老师。当年风华正茂的中年汉子,已经华发初生,渐渐日薄西山。想起当年他老人家对我的冷嘲热讽和吹毛求疵,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其目的也不过是希望我发愤图强,将来有所成就而已,而年少叛逆的我却记恨许久,
华闻读书阁。一声简短的招呼之后,没来得及寒暄,只是瞥见他略显憔悴的眸子中关切慈爱的目光,一如往昔,只是当时年幼无知,没能读懂他看似严厉的要求背后的殷殷关切和浓浓期望,
树海读书阁。一直目送着斯人走出客车车门,落寞地走向那个熟悉的永远只开着小侧门的镇中大门口,我突然有点伤感,瞬间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离开大山好多年了。肉身已然踏进都市,可是灵魂却仍羁留在大山深处,出不去,也不想出去。
4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生长在那个古朴的90年代,我们的条件(不论教育,娱乐,或者生活)的确艰苦了点,但是都能够励志图强熬出来,来到山的外面一展抱负。其实,深山里也有卧龙潜藏,山窝窝里也有凤凰栖身。山里面物质或许贫乏,机会或许渺茫,可能相比于城里的孩子,我们大脑天线接收到的外界信号要弱很多,我们融入社会的适应期要长很多。我们不会熟练地玩电脑,不会优雅地弹钢琴,不会娴熟地跳舞蹈……没有有钱有势的父母亲戚,我们祖辈世世代代是大山的子民。但是我们有一根大山一样刚毅坚强的脊梁,去勇敢担起自己渺茫的未来;我们有一颗黄土地一样博大包容的心,去接纳那个不怎么完美的世界。我们像山间的老黄牛一样,吃着最粗陋的草料,却拼尽全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定地为自己的人生耕耘,为这个世界贡献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
每当想起这些年少求学时的点点滴滴,我都不禁热泪盈眶。我庆幸我是长在大山的孩子。相比于城里长大的孩子,我们的智商并不低多少,我们只是缺少相对较好的成长环境,仅此而已。贫瘠的大山给了我幸福的年少时光,磨炼了我善良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使我更早地成熟,更早地懂得生活的不易,更加珍惜平淡却幸福的生活。走出大山以后很久,再没有年少时候的那种真心的快乐和满足。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也渐渐变得虚伪和冷漠,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谓的“长大“吧。
不管以后混得如何,风光也好,落魄也罢,此生都盼望在老去的时候能回到那个熟悉的魂牵梦绕的小山村,在祖辈世代居住过的老宅里住上一段时日,守着几亩薄田,放养一群牛羊,守候着屋前的青山绿水,重温一段宁静的生活,然后从容地死去,再把骸骨埋在先祖们曾葬着的山谷里。从哪里来就要到哪里去,在这个世界兜完了一大圈,生命终归要回到它最初的发源地;拥着青山,枕着大地,最终化成一抔黄土,重新融入大山,完成一场生死的轮回,这也不失为一种完美的人生告别仪式。
qq:2713096268
相关的主题文章:
你的形象,我的困惑 日子_7 我想你了 岳父、诗人 夏日记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