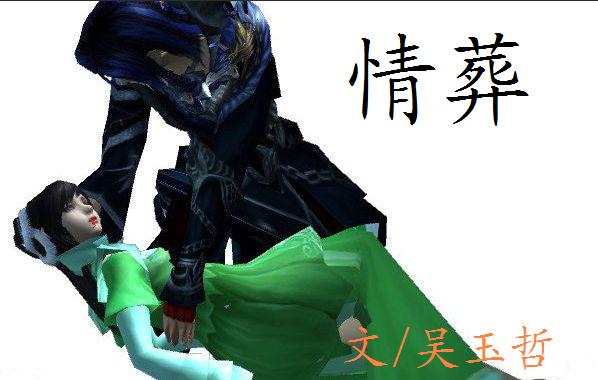说鬼的故事
 ,
铭华读书阁;  ,
树海读书阁;  ,
爱看读书阁; 说鬼的故事
农村人,爱讲鬼的故事,而且都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我从小就怕鬼,比在电影里头看见血腥的战争场面还要怕。白天,从有坟墓的山边通过,我的心都是吊着的;特别是有黄土铺的新坟,连朝它看一眼的勇气都缺乏,
修身读书阁。只要是知道那个地方有了新坟,看没看它,我的汗毛都会“嗖”地突然倒竖。加上我们那个地方葬人没有规矩,死了人想葬哪就葬哪,弄得满地方都是坟,
金霏读书阁,有的死人就葬在离路三尺远的路边,让人胆颤心惊!晚上,我在乡下十几年,从没有个人独自出门的。去队上开会,守仓库,看电影都是结伴而行,或要父亲、哥哥相送。特别是我家通往村子里的路旁边,有一处就有五六座坟,离路也就丈把远,赤裸裸地高耸在路旁,没有树木遮拦。有些坟是我亲眼看见埋下棺材的,我一看见它就会想起棺材里面的尸体,就会想起死去的那个人,
孔子读书阁,好像那个人的尸体永远都不会烂掉,永远都覆盖着白色的尸布,两脚穿着紫红色的老鞋翘翘地躺在里面,连牙齿都是啮着的;甚至还会想起他站在不远的树丛中盯着我,双手做作张牙舞爪的样子,要把我吃掉!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充满了阴冷和恐怖,
广济读书阁!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谁也恐怕说不清,
金门读书阁。相信鬼的存在,是因为说的人多了,流传的时间久了,自己自然而然地就相信了。
我还只有十三岁的时候,曾与队上一个当过乡长的蒋叔叔为集体到洪江去卖辣椒。我担着三十多斤辣椒,走大坪经过哈嘎溪再到岩门再到洪江这条路线。出发时天还没有亮,月亮还在空中挂着,把田间小路照得朦朦胧胧。我挨屁股撵着蒋叔叔走,半个时辰便走到了哈嘎溪的田垄里。
哈嘎溪是我早就知道的地方,沿路没有农舍,知道这地方很不干净,鬼神出没,听说解放前世界很乱的时候,白天都出活的,特别是到了太阳西沉的时刻,如果还有行人过路,那鬼都要蹦出来向行人讨火点烟的,
精彩读书阁,因此我们一般不从这里路过。
蒋叔叔那天抽着烟,黑暗中泛着火星。他不怕鬼,毕竟当过乡长,是个唯物主义者,胆子天大。他担着辣椒停顿了下来,叫我走前面。我巴不得,隐隐的怕意便小了些。我们继续走,
华闻读书阁,走了几根田埂,他就说了,他就直接说事儿,不会叫我的名字。因为乡下的人都懂得,夜晚说事是不许叫名字的,叫了名字会被鬼听到,点子低的就会背时。他说:“对面的山叫做崽儿山。为什么叫崽儿山呢?就是那山上埋了许多化生崽(没成年的人),
树海读书阁。”
我不做声,也不敢往那山上看,心里只觉得对面满山遍野的白色木匣子,满山遍野的小孩在鬼哭狼嚎。我的汗毛倒竖了,我只想蒋叔叔离我近点,甚至离得他与我之间鬼都插不进来。
蒋叔叔又说:“解放前,一到下午这里就有小孩在对面山上喊叔叔,
树海读书阁,要带他回去,他饿死了要吃饭。还有调皮的鬼向行人招手,甚至在行人的背后戳屁股。”
蒋叔叔不怕,在后面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而我从头怕到脚,几乎要窒息在路边了。我只望着我的脚步快点,望着这路短些,快快走出这种阴冷恐怖的沟壑。
还好,箩筐与扁担摩擦的声音在夜空唧唧地叫着,划破了寂静的夜晚,多少为我壮些胆子。这是一种阳声,具有尖利的一面,它与阴对峙,可以驱赶鬼的影子,时时警告鬼神不能靠拢。我索性人为地加大了扁担的上下起伏曲度,这样声音更尖刻些,阳气就荡涤着夜晚的阴气。我一直快速地小跑着,两只眼睛只盯着朦胧的路面,直听到蒋叔叔一声,“现在出了哈嘎溪了”,我才抬头看了看前方。是的,不远处有了光亮,
树海读书阁,山路即将走完,一遍开阔地出现在眼前,近处还有农家的狗在狂吠。这时我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轻松了许多。
哈嘎溪的鬼,实在是只听长辈人说起,并没有亲眼目睹。因此总觉得“鬼”的存在,只是一种传说。不过,半年之后的一件蹊跷事就让我永远难辨是非了。
同样是十三岁这年的夏天,我像往日一样,到离家两里路远的一口水井里去挑清凉水。由于挑的人很多,要按先后次序舀水,轮到我舀好水回家时天已经黑了。那晚,父亲、哥哥没来接我,逼得我独自回家。当我走过老阉猪匠的家门口时,就要下一个坡,下了坡再过三十米就要通过一片坟地,坟地前面不远就是我的家。但我刚下完坡,
树海读书阁,抬头往前一看,还容不得我思考什么,我丢下担水的竹筒筒就往回跑,一直跑到阉猪匠家里。
阉猪匠是位老人,他有驱鬼信神的本领,因为和我是家门,
孔子读书阁,我们叫他来虎公公。来虎公公见我惊慌失措的跑来,马上迎了过来。问我:“你气喘嘘嘘地干什么了?”
我缓了缓气,然后说:“不好了,那边有鬼!”
来虎公公说:“你小伙子尽讲鬼话,哪里有鬼呀?”
我说:“真的有鬼。好高好高,有电杆那么高,那么瘦,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背着手,在路右边的菜地旁站着不动。现在可能还在那里,
树海读书阁!”
“小雀,你去看看。”来虎公公吩咐着他第三的女儿。
小雀,我们称她为雀姑姑,年纪比我长一岁。雀姑姑拉着我的手就往屋外面跑。我们自然是不敢跑到我丢竹水筒那地方去看的。我们只要在她屋前的路边朝前一看就能把前面的路况观察得一览无余。雀姑姑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往路边挪动着,将头伸得老长老长向前窥视。
我终于看见了,雀姑姑也看见了。鬼不在原来的地方,已经走过来了,依然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依然还在我必须通过的路上,依然背着手,在观察路边地里的生产一样。雀姑姑的胆量比我大,足足朝鬼凝视了一分钟,看得仔仔细细。这时我也不怕,抓住雀姑姑的手,生怕她把我甩掉,紧紧地抓着,在她屁股后面朝前观察。雀姑姑终于不再敢看了,她说:“快走,
金门读书阁,再看,鬼就到我们身边了。”我拉着她的衣角就往回跑,俩人一路小跑到了家。
来虎公公见我们回来了,忙问雀姑姑:“没有鬼吧?”
雀姑姑忙说:“有,有,有!真的有!现在已经走到这边路上来了。”
来虎公公说:“你们小孩尽讲鬼话,世界上哪儿有鬼呀?那是月亮被树遮住的影子,月亮越斜,影子越长。哪里有什么鬼哟?”
“走吧!我就不怕鬼,送你回家,看到底有没有鬼?”来虎公公说完,就把他秋年四季带在身上的那根三尺长的,
金霏读书阁,脑壳包了铜皮的老竹烟筒捏在手上,起身出了门。听说他的老竹烟筒很神奇,
华闻读书阁,很压邪,鬼只要闻到了它的气息,就会逃之夭夭。
我撵在来虎公公的屁股后面,在他的后面走我的胆子大了很多。上了我走的那条路,下了坡,没有半分钟就到了我丢水筒的地方。来虎公公说:“你就是在这里看见鬼的吧?哪里有鬼呢?哪里有鬼呢?我就知道你们崽伢子尽讲鬼话!”
我不做声,默默地跟着他走。前面空荡荡的,路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月亮照泻下来的光辉把路面映得黄白黄白,连路过那群坟墓旁都显得比平日格外静谧。
我奇怪了,就像泼了一盆雾水在头上,
精彩读书阁,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世界,几分钟以前的东西,竟变幻的让我那么莫测。我的内心对眼前的事实是多么的不服!总怀疑那个“鬼”在来虎公公的威慑下,藏匿在不远的树丛中,藏匿在路坎脚,或者化作了一抹白光混进了月亮的光辉之中。
来虎公公将我送到了家,还很耐烦地给我压了惊。压惊就是在我的头上不断地划着十字架,口里不断地念叼着咒语,
宁静读书阁,时而拍拍我的背子,时而摸摸我的脑袋。说来也怪,他就像一位心理医生,帮我这样做了调理以后,我心里的恐惧感就随着他的几拍,烟消云散了,
树海读书阁,心理真的就显得轻松而又安然,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未曾发生。
长大以后,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屋连着屋,灯映着灯,人碰着人的城里。在城里鬼的故事自然很少,
精彩读书阁,即使听人讲起,也都是从乡下捡来的,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我后来开上了大货车,每天都奔驶在乡村里,在万里运输线上。白天、黑夜,阴冷的峡谷前,林涛呼啸的丛林里,都要独立而行。时间久了,有些司机们爱讲鬼,鬼的故事在不经意间又会传到我的耳旁。这些故事每当我把它与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时,我就觉得“鬼”的故事很玄,
树海读书阁,它不只是我一个人所闻,也不是我一个人所遇,是一个世人永远无法被认可或否定的传说。正如大家所说,信者有,不信者无。
我曾经的同事覃,与我是老乡,在单位又恰好住我的隔壁。他是一个老司机,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后,还保留着部队军人那种很豪爽的作风。鬼这样的故事,作为曾是军人的他,过去谁讲起他都不削一顾。现在他虽然已经死了三十几年,但他在死之前曾给我讲述的一次鬼的故事至今都很难忘怀。
他有一次到长沙运货回家,在路过雪峰山脚的大坪南溪冲时,
树海读书阁,夜已经很深了。这时不知什么故障,车子嘎然熄火。虽然夜已深深,那种莫名的恐惧掠过心头,但也没有丝毫办法,车坏了就得下去修。
他借电筒的光亮,揭开了引进盖,打开了分电器盖子(老式解放牌),查看“白金”是否有问题。他刚好从兜里抽出张一角新币擦了擦白金,调了调白金间隙,这时旁边猛地出现了一个小孩沙哑的声音。小孩说:“叔叔,我要搭你的车回去。”覃听得很清楚,赶紧循声望去,但在电筒的扫视下,黑暗中什么也没发现。这时惊吓的覃才猛然发现,自己的车坏在了一个叫崽儿弯的鬼地方。这地方关于鬼的传说他早有所闻。听见小孩在说话,他顿时毛骨悚然,全身生满了鸡皮疙瘩。幸亏他手上拿着铁锤,顺势在发动机旁的大梁上狠狠地几敲,敲起的尖刻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也壮大了他的胆。他迅速盖上引进盖,跳了下去坐到了驾驶室,把车开得飞似的。
不到半小时他的车行驶到牛泥坳。这地方离家只差四公里,是一个极阴冷,传说鬼神极活跃的偏僻地方。他只要爬过十几米陡坡,就可以看见镇上的一片灯火了。但正当爬行在陡坡的中间时,
树海读书阁,路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带斗笠的矮小孩。小孩不说话,挥舞着小手,意思是要搭车。
这一幕又把覃吓得神魂颠倒,
爱看读书阁,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又是深更半夜了,一个小孩子此时带着斗笠在这里干啥?他紧紧地盯着那个小孩,准备从他身旁绕过去。可是,车子真的快到小孩身边时,小孩就像电影戏的镜头一样,突然不见了身影。他把车前的所有大灯统统打开,睁开大眼,在车灯所及的视野中全力搜寻,还是一无所见。
那夜,覃没有睡觉,睁着眼睛想了大半个晚上。因为从部队回来的人大都不会相信鬼神,骨子里就被部队熏陶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但在同一个晚上,连续碰上了两件同一个内容的邋遢事,不能说不让他辗转难眠。
从此,覃一振不起,人变的晕晕呼呼,就像霜打的茄子嫣嫣的,早已失去了一个年轻人的朝气蓬勃。
半年之后,他终于一病不起。到医院检查,说是患感冒,给他输了五天的抗生素就奇迹般的好了。在家再休息三天,又准备驾驶他那辆解放牌货车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
孔子读书阁。可是三天未到,高烧又来了,全身打摆子,给他盖上五床被子也不能驱走他骨子里的寒气。来到医院,医生又把他们的抗生素用上,从早输到晚,覃的烧就是退不下来,人就像是掉到了冰库里,直打哆嗦。
幸好覃的父亲是那时的县革委委员,他的出面给这个医院增加了压力。院长马上组织医生会诊,一会诊就觉得不对头,覃的病与那种“出血热”相似。于是医生急了,院长急了,小覃父亲更急,单位上的领导也急得五心不做主。
“出血热”不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所能治得好的病,他们迅速与治“出血热”的专科医院——溆浦县人民医院取得了联系。为了救人,他们双方商议:溆浦用车把医生送到溆浦至安江的路中间——黄茅园;安江的车由他父亲负责,在县革委派一辆小车到黄茅园去接。一场接、送医生抢救覃的战斗打响了。
医生终于在三个小时以后赶到了。他们水米未进,从车上跳下来,就直接奔向了病房。他们拿着听筒,在覃的胸脯上听了又听,把眼皮子往上翻了又翻,然后就叹了一口气,走到医生办公室遗憾地说:“最多只有两个小时了。”
但溆浦的医生并没有因此就停止了对他的抢救,我记得,将他们带来的药物全用上了,光输液瓶就吊了四只,四肢齐来。由于覃年轻气盛,他并未完全昏迷,而是难受得在不断地挣扎,医生为了输液的安全,要求我们单位派了四个年轻小伙子捏住小覃的手脚,避免他动弹。我也参入了捏脚的行动。
溆浦医生还没有来两个小时,我们捏脚的四个人只听得覃猛地一抽筋,做了最后的垂死挣扎状,四肢神经就突然松弛了,然后就直直地摆在了白色的床单上。
覃就这样走了,年仅二十八岁。他把鬼的故事留了下来。是真的,还是假的,一直困扰着我,也困扰着知道覃这个故事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发现鬼,也没有听到新的鬼的故事了。
相关的主题文章:
【原创散文】生活碎片_1 打油富豪移民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二十岁生日 太阳村的故事(报告文学)